文章
房慧真/自由即奴役,父權是好的權力──導讀《喬治.歐威爾之妻的隱形人生》

還原「妻子」在西班牙內戰裡的角色,將艾琳身上的虛線描成實線,再塗上顏色,給予喜怒哀樂表情,是《喬治.歐威爾之妻的隱形人生》整本書最精彩也最具顛覆之處。艾琳是左翼思想的捍衛者,一開始她也像全世界的左派、安那其、無政府主義者一樣滿懷理想,急著想要起身奔赴西班牙,和工人一起對抗保皇派的獨裁者。歐威爾卻說,我一個人去就好,妳必須留下來顧雜貨店,照顧牲畜和菜園,幫忙校稿還有聯絡編輯。離別之前,艾琳還幫忙典當家傳的銀器,幫歐威爾籌措旅費。其後,艾琳透過親戚幫忙,前往巴塞隆納擔任英國獨立勞工黨(ILP)的祕書,ILP和西班牙當地的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關係密切。艾琳身處於ILP與POUM的行動核心,還不曉得山雨欲來,巴塞隆納從大後方成了前線,POUM成了史達林除之而後快的眼中釘,史達林透過祕密警察與間諜深入西班牙內戰,埋伏在艾琳工作的辦公室,報告一舉一動。
艾琳在歐威爾書中的角色,是連配角都不如的路人甲。然而,當歐威爾在前線受傷,子彈穿過脖子,艾琳行動力十足,在48小時內馬上趕到,並向在倫敦行醫的哥哥求助,歐威爾在書中花費了2,500字的篇幅寫受傷,艾琳卻被隱身了。「我的妻子」像一抹蒼白的幽靈若隱若現,是個奇怪的存在,歐威爾絕口不提艾琳在巴塞隆納有工作,而且是極具危險性的政治工作。「有時候,略而不談會讓事情變得很奇怪,因為他在字裡行間拚命遮掩她的存在。」
1937年6月,史達林遙控下的鎮壓,由西班牙警方執行的大抓捕即將開始,POUM的成員陸續被拘捕、刑求,甚至被殺害。同事勸艾琳趕快離開,艾琳卻害怕若歐威爾從前線休假回來將自投羅網,她決定留下,每天像座雕像一樣坐在飯店大廳視野最清楚的地方,從白天到黑夜,她望眼欲穿,唯恐歐威爾將會在飯店前方下車,從鍍金浮雕的大門走進來,連眼皮都還沒眨一下就被逮捕。她沒有意識到自身比歐威爾更危險,但艾琳無疑比歐威爾重要多了,她連繫核心人員、保管護照、經手所有的物資彈藥補給,而歐威爾只是前線的一介民兵。可到了書裡,艾琳無足輕重,「我的妻子」僅僅只是史達林的黨羽要引歐威爾出來的誘餌。
西班牙內戰中的「左派內部鬥爭」,讓歐威爾的書有了新鮮且鋒利的切入角度,讓他成為20世紀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影響至今。然而「左派內部鬥爭」都是陷在漩渦中的艾琳一一轉述給他的,「被抓的人是她的同事,而四處傳播的謠言,還有俄國間諜在腰帶上掛著炸彈裝飾在會客室裡昂首闊步,這些事都是她告訴他的。她自己也含糊成了『我的妻子』,她的所作所為、所知的一切似乎都任由他擷取。」1938年新年元旦,歐威爾夫婦已逃出西班牙,平安回到瓦靈頓的家。艾琳幫忙打字,彷彿又在「文本」裡被殺死了一次:
「她確實在這個故事裡,卻永遠不會有人看見,就像鷹架或骨架一樣,消失在最終的結果裡,或者遭到覆蓋。」
歐威爾在婚後完成的《向加泰隆尼亞致敬》、《動物農莊》、《一九八四》,這三本書證明歐威爾的洞燭先機,提前預知史達林的邪惡,當時整個文明世界都把目光瞄準納粹黨希特勒的崛起,只有歐威爾從「巴塞隆納大清洗」看到極權主義的起源。前兩本書寫於艾琳還在世時,有她的經歷與深度參與討論,艾琳在1945年因為幫歐威爾省錢而選擇非倫敦的醫院開刀,不幸身亡。妻子過世後,歐威爾開始動手寫《一九八四》,書名之所以叫「一九八四」,以往常見的解釋是1948年倒過來成為1984,這都無法解釋書的初稿完成於1947年,出版於1949年,和1948年沒有明顯關係。後來我們才得知,艾琳在1934年就發表了一首反烏托邦的詩〈世紀之末,一九八四〉(End of the Century,1984)。這或許是歐威爾懷念艾琳的方式,但不代表他的愛堅定如一。艾琳在世時,歐威爾反覆外遇劈腿,艾琳過世後短短一年間,歐威爾至少撲倒4位女性並向她們求婚。他發覺請一個女傭遠遠不夠,「他根本不太認識她們,但是他有書要寫,於是就有了職缺。」
艾琳和歐威爾曾經討論過一個議題:若是莎士比亞在明日重返人間,人們卻發現他最喜歡的消遣是在火車車廂裡強暴小女孩,人們要選擇犧牲小女孩還是下一部天才巨作?歐威爾站在偉大作品那邊,而艾琳惦記著小女孩。除了莎士比亞,還有會性虐待妻子的達利,比起達利驚世駭俗的程度,歐威爾的情節僅是頻繁劈腿和冷落無視、在作品中取消妻子,有那麼嚴重嗎?有需要到「取消文化」的程度嗎?這也是安娜.方德要問的:如果知道自己喜歡很久的作家其實是王八蛋,那怎麼辦?方德不覺得要到一筆勾銷的地步,她只是想用歐威爾的「雙重思考」去回問──歐威爾在《一九八四》裡說:「雙重思考是指一個人心裡可以同時抱持著兩種矛盾的信念,且兩者都接受……必須清楚意識到這個過程,否則思考後的結論就會不夠準確,但是又不能意識到這個過程,否則會覺得自己在造假,就會有罪惡感。」一個深入探討殖民地、極權國家行使權力方式的作家,為什麼可以同時接受父權徹底輾壓女性?歐威爾在小說裡這樣說:「這套欺瞞心智的系統非常龐大複雜。」「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是《一九八四》裡著名的「新語」,或許可再加上一句「父權是好的權力」。
方德發覺整個文壇成為共謀,男性作家愈偉大愈重要,他們身後輪轉的十個太陽就會把任何陰性空間都吞噬殆盡。從上一代開始,歐威爾的母親、阿姨都是非常活躍的婦權運動者。歐威爾對於公平正義的重視無疑來自母系的影響,「要如何強行消失一名女性?歐威爾的傳記作家先從基本的抹除開始,例如他傳承自母親那邊的文化及知識才能」。方德進一步提到,「傳記作家之所以忽略那些女性,是因為歐威爾自己也抹除、模糊了他生命中的女人。」傳記作家強作解人的還有,歐威爾夫婦從西班牙內戰回來後,到北非放鬆身心,歐威爾自述,他在馬拉喀什找了一個十幾歲的阿拉伯雛妓。該怎麼解釋作家的嫖妓行為?傳記作家提出三種解套的方式:一、那是歐威爾口頭吹噓,非事實。二、時間安排上根本不可能,沒發生過這件事。三、有發生過這件事,但那是艾琳同意的。為了替歐威爾開脫,傳記作家還說,艾琳在巴塞隆納曾和別人有一腿,進而推衍夫妻同意開放式關係。
正如方德在書中所說的「父權魔術」,「首先是要讓她所做的事情消失(這樣看起來全部都是他獨力完成的),再來就是讓他對女人所做的事情消失(這樣他就是無辜的)。這套魔術就是父權體制中那顆黑暗的、雙重思考的核心。」
Chinese Bronzes Blur the Line Between Original and Copy 中国青铜器模糊了原作和复制品之间的界限
这里一个未解决的紧张关系是当代博物馆概念与中国传统之间的根本不可通约性。前者通常珍视具有可识别制作者的独特物件,而后者中,复制至少在20世纪之前一直具有截然不同且受人尊敬的含义。例如,6世纪的历史学家谢赫将“传移模写”编纂为中国绘画六法之一,而元代(1271–1368)哲学家赵孟頫则认为,临摹过去的伟大艺术品可以保证文化的有机延续。在生产青铜器和陶瓷的作坊中,铭刻名字是为了质量控制,而不是为了将特定物件标记为个别艺术家的作品。(有趣的是,这种分野比人们想象的要年轻;早期的美国博物馆里也摆满了欧洲艺术品的仿制品。)
本次展览中,尽管一些为皇室配对的书写工具展示了表明它们“仿古”的标记,但标签澄清了它们“与古代作品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展览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两件作品在中段出现:两盏鹅足灯(就像它的字面意思一样——形状像鹅脚的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0 年代,以及 1800 年代的复制品。墙上的文字告诉我们,这件作品是由“当时最著名的古董商之一”委托制作的,但费尽心思强调其铭文“明确表明它被创作出来是为了艺术上的致敬,而不是伪造”。是什么让某物成为“致敬”而不是“伪造”?皇帝徽宗委托制作的许多模仿古代青铜器的作品是“伪造品”吗?在将当代艺术品等级应用于具有不同价值的传统时,本次展览确实是在重塑过去。
150年后再看米勒“土地上的生活”,有劳作更有人性


他于1859年创作的画作《晚祷》(The Angelus),现从法国巴黎奥赛博物馆借展至英国国家美术馆。仔细观察画中的人物,会发现他们格外怪异。他们的脸庞模糊,在不合身的工作服下,展现出令人着迷的身躯。他们年龄几何?彼此之间有何关系?男人相当年轻,衬衫最上面的纽扣松开,但穿着厚厚的粗布裤,双腿僵硬得像个洋娃娃。女子的年龄则更难判断,因为她侧身站立,微风吹拂着厚重的裙子,双手紧握。他们或许是一对夫妻,又或许如这幅作品的忠实粉丝萨尔瓦多·达利所说的母子。他们的肉体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一场景刻画更是让人觉得:工作日结束了,他们正在祈祷,终于休息了。但如果他们是母子呢?则可以去看看达利对其的理解。
达利对米勒的《晚祷》非常感兴趣,揭示了隐藏在作品中的人性、欲望及潜意识思想,并据此创作了许多作品。达利认为,米勒最初在前景中画了一座坟墓。你似乎能看到它。他说服卢浮宫对这幅画作进行X射线检查,并声称检查结果证实了他的理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还撰写了《米勒<晚祷>的悲剧神话》,并在30年后出版。由此,米勒对于《晚祷》的描绘,与其说是宗教性的,不如说是带有情色意味的。《晚祷》是他描绘法国农民爱情故事的巅峰之作。米勒毕生致力于描绘农村贫民,这是一个被剥夺了完整人性的阶层。他描绘了辛勤劳作的生活,但他想让你看到,在锄头的背后,是一个有思想、有身体、有欲望的人。

【投書】陳斌全/節慶城市的反思:觀光、文化環境與文創發展的三方挑戰
過去20餘年間,台灣各地以辦理與文化、藝術相關的活動,帶動觀光旅遊人潮,藉由外部的消費以促進在地經濟,已成為各級政府凸顯政績的重要手法。
幾個比較早期的例子,如:1993年開辦的「嘉義管樂節」、並在1997年更名為「嘉義市國際管樂節」;1996年為慶祝宜蘭開墾200週年的「宜蘭國際童玩節」開辦,後來成為在地特色活動;還有如於2000年由當時的台北縣政府(今新北市政府)與民間唱片公司共同創辦的「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成為國內以流行音樂創作為內容的夏季大型活動濫觴。
也有爭取國際大型展會, 進行城市行銷以提高國際知名度的例子,如:台中在2018年曾舉辦「世界花卉博覽會」;或是由交通部觀光局(今交通部觀光署)於1990年所創立的「台北燈會」,後於2001年始巡迴至不同縣市辦理,並於2003年起定名為「台灣燈會」,逐漸成為當時觀光局對國際行銷台灣觀光的焦點節慶。
時序來到2025年,台灣一年有多少以「節慶」為名的活動?目前似乎很難找到相對精確的公開數據,但由交通部觀光署透過評選推薦機制所選出、登載在《台灣觀光雙年曆(2024-2025)》的資訊可見,列為「國際級」的節慶共有40項,而列為「全國級」的節慶則有68項;其中有傳統的宗教、民俗相關慶典,也有以藝文或消費性內容為主所創設的「新興節慶」。另一方面,在《觀光雙年曆》的節慶中,不少與公部門的資源、補助等連結,如:「國際級」的各項藝術節、嘉年華會或博覽會,以及「全國級」以各地方為名的燈會;可以合理推論的是,在表列中能看見的傳統宗教、民俗、豐年祭等相關活動,也有公部門資源的補助。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以文化或藝術內容作為促進觀光的作法,對中、長期制度建構的想像較少著墨,而是以活動單次成效與數據的累計為主。因此,運用「地方建設」發展新的項目以服務觀光需求,或是藉由觀光以強化地方的原始脈絡、使地方的「文化主體」成為吸引遊客的主因,是需要釐清的課題。本文的目的並不在於批判觀光的發展,或是視「節慶」的辦理為負面因素,而是想提出一個思考方向:「文化環境」與「觀光」的相伴相生,如何以多數居民的日常需求為優先?如何在舉辦節慶的同時,設計導向實質文化環境累積的機制,讓節慶的辦理成為形塑在地文化的新元素,促進未來文化創意相關產業發展的養分?

「愛丁堡國際藝穗節」(Edinburgh Festival Fringe)是目前全球規模最大的表演藝術節慶,執行長麥卡錫(Shona McCarthy)女士剛於2025年3月卸任;她卸任後接受訪談指出,當藝文活動逐漸因為規模擴大,部分演變為「觀光化」後對所在城市帶來衝擊,城市的公共治理除直接獲得藝穗節所帶來的益處外,並未積極輔助節慶的合理健康發展;特別是在2022年COVID-19疫情結束後,蘇格蘭的旅遊市場呈現報復性回復之際。
愛丁堡藝穗節並不是愛丁堡市議會以公共資源支持的節慶,運作所需主要由藝穗節自行籌措。麥卡錫接受英國《衛報》(The Guardian)訪問時指出,2024年愛丁堡藝穗節售出260萬張門票,卻未獲得相應的基礎設施支持;藝術家和工作人員難以負擔住宿成本,市中心通訊盲區影響遊客即時訂票,當地公共交通系統亦無法有效支撐同期活動規模。
她也揭露市議會過度收取權利金:「架一個舞台,就要收1,000英鎊(約新台幣40,000元)的許可費;封街舉辦活動就得按路邊停車格的費率計費。」這種把節慶視為搖錢樹的治理思維,與將文化視作城市策略定位,形成鮮明對比。她對媒體強調,疫情後的重整應回歸節慶本質:自由表達、文化民主、觀眾參與的核心價值;藝穗節並非只是賣票推廣的行銷平台,而是「文化實踐的場域」,容許冒險、實驗、生成文化連結,並且已是愛丁堡的共同體,不能被以「景點」看待與行銷。
另一方面,隨著大量遊客湧入愛丁堡,過度的觀光壓力侵蝕城市的生活機能與文化生態,如:短期租賃平台興起,使得本地住房供給緊縮;遊客集中的愛丁堡舊城區因觀光汙染,使得居民被迫遷離──這些都是「節慶城市」所產生的雙面刃效應。
運用文化和藝術內容所創造的新興節慶,是否只能朝向「觀光」導向,難以連結商業之外的發展目標?歐盟的「歐洲文化首都」(European Capitals of Culture)和英國的「英國文化之都」(UK City of Culture)計畫或許可為借鑑。
「歐洲文化首都」為歐洲聯盟自1985年起推動的重要文化政策,目的在於透過以「城市」為單位的全年度主題策展與文化活動,強化歐洲各地人民對文化多樣性的認識,鼓勵城市以文化為核心,重新思考其發展願景與地方認同。透過主動提案爭取機制,獲選的年度城市將獲得來自歐盟的經費與媒體資源,並且負有向全歐洲和全世界展示其文化特色與創意的任務。
這項制度鼓勵中、小型城市跳脫「觀光導向」的活動規劃,思索文化如何實質改善居民生活與城市治理。2025年的歐洲文化首都分別為德國的肯尼茨(Chemnitz)與斯洛維尼亞的新哥里察(Nova Gorica),兩者皆選擇以區域文化合作與跨國共創為年度主軸,反映出歐洲在後疫情與地緣政治轉型時代,對於文化治理的想像。
上海博物馆“两塗轩”升级,宋画《秋山萧寺》领衔
記憶才是歷史的安魂曲:高砂義勇隊與3枚「猛2689」兵牌80年的終戰歸鄉記
2025年8月是二戰終戰80週年。80年前戰爭的結束,雖終結了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卻引發另一層身分矛盾──戰時屬於戰敗國的台灣,戰後因中華民國政府的接收,轉入戰勝國之列。於是,當這個國家長年以「勝利」、「光復」等論述掩蓋戰時台灣人民的多重角色,又在威權體制下壓抑個人記憶與言說時,屬於台灣社會的戰爭經驗與創傷,也逐漸被遺忘和割裂。
在所有被忘記的歷史中,高砂義勇隊的故事尤其沉寂。作為日軍徵召、派往海外作戰的原住民部隊,他們不僅在語言與文化上處於弱勢,戰後也難以在以漢人為主體的社會中留下記憶。即便近年來關於台籍日本兵的討論逐漸浮現,高砂義勇隊的身影相較之下依然稀少,研究與記述更因當事人的凋零而陷入斷層。
在終戰80週年之際,《報導者》專訪長年深耕台東都蘭部落、熟悉高砂義勇隊歷史的國立史前文化博物館館長蔡政良。2009年,他前往新幾內亞島進行田野調查,帶回3枚日軍兵籍牌,並於2025年正式登錄為史前館館藏──這也可能是第一批由台灣人從海外戰場親手帶回、且極可能屬於高砂義勇隊的戰爭遺物。這段記憶,卻得從一段「老人不說、年輕人不問」的高砂義勇隊故事講起。
1920年出生的高仁和,是都蘭部落的阿美族。他這一生有3個名字:出生的時候,父母為他命名「洛恩(Ro’en)」;在日本殖民政府皇民化運動下,他是「吉村務」;「高仁和」是他從戰場上回來後,中華民國政府讓他改的名。
他是在1943年上戰場的,但參戰並非出於他的志願,而是被指派。當年才23歲的洛恩,某日與族人們結束了監控敵機的警戒工作,正準備交接時,突然看到警察朝他們走來,劈頭就說:因為表現優秀,他們4人已被指名加入第五梯次的「高砂義勇隊」。
高砂義勇隊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殖民政府動員台灣原住民前往南洋叢林作戰的志願兵。1941年末,日本偷襲珍珠港後,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為了獲取戰爭資源,日本將戰線延伸至印太地區。由於原住民過去對抗日軍的驍勇善戰及適應叢林戰鬥的能力,日本政府遂於1942年至1944年間成立了「高砂義勇隊」,並分8次徵召數千名台灣原住民青年,派往太平洋各島嶼隨日軍作戰。
從洛恩的角度來看,自己入隊後的地位確實有些提升──年輕的青年團員對他(們)投以尊敬的眼光,平時頤指氣使的上層階級青年也變得客客氣氣。原本經常欺負人、動輒拳打腳踢的警察,現在更是畢恭畢敬,對他們的家人也和顏悅色。儘管在派出所的造冊中,這些高砂義勇隊員的職稱是「傭人」,但不知情的洛恩等人,仍因此獲得了一些尊嚴。
1943年4月初,洛恩等人在台東糖廠與其他部落的原住民集合,搭上軍車前往高雄港搭船出征。這一幕被當年還是小男孩的林哲次看見,並深深留在他的記憶中。
後來,這個小男孩長大,成為台東多所中學的校長,並在82歲時,憑藉對高砂義勇隊的研究,於2011年取得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碩士學位,還翻譯了一本高砂義勇隊員的日記。而他的指導教授蔡政良,則在年輕時因緣際會成為洛恩的乾孫,甚至於2009年與洛恩的兒孫一同前往洛恩曾經親歷的戰場,將屬於高砂義勇隊的兵籍牌帶回台灣,尋找這些名牌的主人。
不過,當時還是博士生的蔡政良,由於無力處理,便將這些兵籍牌捐贈給國立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彷彿命中注定,這3張兵籍牌在他借調至台東史前博物館擔任館長時,終於在終戰80年的今天,正式成為史前館的藏品,回到屬於原住民的山海懷抱。
兵籍名牌回歸的故事,起源於2005年盛夏的某個傍晚。當時,正在清華大學就讀人類學博士班的蔡政良,與乾爹──洛恩的兒子Kapah(漢名林昌明)在庭院裡抽菸、吃檳榔,喝著保力達聊天。在茂盛的海檬果樹包圍的涼亭下,Kapah突然對蔡政良說:「阿公(洛恩)吃過人肉喔。」
蔡政良雖然驚訝,但思及Kapah素來說話跳躍又愛開玩笑,便也以輕佻語氣回應:「是嗎?這有什麼了不起,我三峽的同學也告訴過我,他阿公的阿公曾經吃過泰雅族的人肉。」
「吃人肉」的故事對蔡政良並不陌生,他曾聽過在時,被埋在地底的礦工為了求生,吃掉喪命同伴的屍體而存活下來的故事;也在書中讀到過「吃虎肉毋驚老虎,吃番肉毋驚番」的俗語,知道台灣漢人曾有食用在武力衝突中喪命的原住民人肉的軼事。只是這些故事發生的時空對他來說相當遙遠,並未讓他產生太多感受。至於洛恩阿公吃人肉這件事,雖然勾起了他的好奇,但他表現得不以為意。
「我是跟你說真的啦,不然你自己去問阿公!」Kapah態度轉為認真地說。
蔡政良走進客廳,只見洛恩專心地看著電視上的女子摔角,於是拉張塑膠椅坐在旁邊,等待機會。等到廣告時間,他立刻詢問阿公是否吃過人肉。洛恩只回答:
「對啊,在Niukinia吃了一個白人。」

到了1944年2月,當初承諾的志願軍服役期限即將屆滿,眾人也準備前往日軍的海軍基地搭船返台,結束高砂義勇隊的軍旅生涯。長期飢餓導致體力虛弱的洛恩,當時更因即將回家而充滿期待。
部隊拔營東行不到一天,便發現了美軍的蹤跡,眾人不得不緊急撤退,躲入山區叢林。洛恩一行人在原始密林中穿行好幾天,當大家幾乎被飢餓與疲憊逼入絕境時,眼前終於出現了一條溪流。順著溪水望向南方,一處山坡地映入眼簾,坡地後方有個平台,平台背後則是一座綿延起伏的山脈。此時,隊長才下令部隊就地紮營躲藏。
躲在山區的日軍部隊,能取得的食物與鹽分愈來愈少。原本就身形清瘦的高砂義勇隊隊員們,不僅面黃肌瘦,不少人更因瘧疾倒下。儘管高砂義勇隊員們曾提議外出打獵捕食,但帶隊的日軍長官擔心槍聲暴露行蹤而嚴令禁止。無可奈何之下,洛恩只能瞞著長官偷偷設下陷阱,偶爾捕捉當地一種與鴕鳥差不多大的食火雞。
某日,洛恩與幾位高砂義勇隊員奉命下山,試圖找尋日軍補給。途中,他們發現一處原為日軍所屬、卻已被美軍占領的軍營。眼見形勢危急,且實在飢餓難耐,眾人萌生了冒險潛入美軍陣地偷取食物的念頭。「反正餓死和被槍打死都是死,不如冒險試試看吧。」然而洛恩的賭命一搏,卻只偷回了根本無法充飢的バター罐頭(美軍奶油罐頭)。
幾名高砂義勇隊員沒找到補給,卻帶回了日軍基地已經失守的消息,士氣頓時墜入谷底。誰知,發覺物資被竊的美軍,隔日竟循著蹤跡找到了洛恩一行人在深山裡的營地,負責警戒的洛恩一見美軍出現,便立刻開槍,一名美國大兵應聲倒地,其他美軍隨即撤回叢林裡──這是洛恩自「出征」以來,第一次朝敵人射擊。
「阿公跟我描述這段的時候,神情很亢奮。」蔡政良回憶道,當時洛恩的表現與以往不同,這次他不再像以前那樣需要追問,才能擠出一點破碎的回憶,洛恩當時興致高昂,是邊喝著保力達邊比手畫腳,暢談當時的情景。
然而,洛恩開的這一槍引起不遠處營區裡的隊長注意,他判斷「美軍即將來襲」,並下令全員備戰。果然,美軍來了,雙方旋即激烈交火,但由於日軍占據地形優勢,美軍無法迅速攻克,也不敢戀戰,最終匆匆留下了另一具陣亡士兵的屍體,再度撤退。
戰鬥結束後,虛弱的洛恩硬撐著埋葬了陣亡日軍,突然察覺遠方有一群高砂義勇隊員正在聚集,像是在議論著什麼。他好奇地擠進人群中細看,才發現大家已經餓得再也受不了,於是有人拿出山刀,準備分食敵軍留下的兩具屍體。
「根據洛恩阿公描述,這就像殺豬一樣分食。」由於原住民祭典時常會殺豬,蔡政良也仔細向我描述了殺豬的步驟和方法,表示這些日軍(高砂義勇隊)也是以同樣的方式肢解人的屍體、火烤烹食。
洛恩雖然非常飢餓,但此刻仍極為猶豫,不知自己究竟該上前搶食還是轉身離去。這時,那位以流利刀法肢解美軍的布農族隊員,從火堆旁抓起一條手臂下半部,遞給洛恩和他旁邊的同伴:「很好吃啊,我的朋友,這個給你們吃。」
「餓過頭的時候,他覺得人肉和豬肉一樣好吃。」蔡政良轉述洛恩的看法,說道:「沒辦法,那時候真的沒東西吃。」
事實上,在日軍資料中,也廣泛記載了戰場上的食人事件。像是紀錄片《怒祭戰友魂》(ゆきゆきて、神軍)中,就提及日軍食用新幾內亞當地原住民,甚至同袍的肉。日本作家林榮代也在《台灣第五回高砂義勇隊:名簿・軍事貯金・日本証言》一書指出,許多因無法忍受當地戰況而自殺的日軍,最終被飢腸轆轆的同袍吃掉,甚至被裝進罐頭裡。
而洛恩吃的是「白人」的肉。這是洛恩第一次吃人肉,也是最後一次,那天之後,他們又回到繼續挨餓的日子。直到1945年的那天,一群日本軍官突然現身,要求部隊解除武裝、聽從美軍命令──因為日本天皇已經宣布敗戰。
地獄般的戰爭終於落幕,洛恩也被送進盟軍的戰俘營。雖然他們是敗戰者,但至少這裡有固定的食物,生活比在山上好多了。到了1945年12月,洛恩終於返回都蘭時,當年一起被指派加入高砂義勇隊的4位同鄉青年,卻有一人再也無法回家。
蔡政良是新竹客家人,自有記憶以來,便跟著阿公住在一個以客家族群為主的社區,雖說如此,住戶中也有不少外省老兵,而這些參與過抗日戰爭或國共內戰的士兵,隻身來到這個曾被日本統治的地方,有的娶了原住民,有的則是獨居。國小時,蔡政良與一位獨居的外省老兵最為親近,但因年紀太小,無法主動詢問,且老人也不曾多談自己的過往,因此,無從得知這位阿公的故事,「我覺得他們(老兵)有個共同的特色,就是話都很少。」
無論是自己的阿公、外公,還是鄰里的外省老兵,都在蔡政良年輕時去世──等到他開始產生想要了解他們的戰爭經驗和人生的意識時,已經來不及了。但洛恩阿公不一樣,當蔡政良得知他「吃人肉」的事情時,他已經是個熟悉台灣文史、並被接納為都蘭部落一分子的博士生,更能進一步追索洛恩的戰爭經歷。
蔡政良帶回來的,不僅有3張日軍兵籍牌,還有紀錄片素材和書寫的材料。2009年夏天,紀錄片《新幾內亞到台北》在原住民電視台播出後,台東金峰鄉排灣族介達部落首領高正治(Gui Giling)找上蔡政良,希望他能再去新幾內亞一趟「幫他把舅舅的靈魂找回來」。
1950年出生的高正治是一名醫師,曾擔任國大代表,並因為在修憲案中提議以「原住民」取代「山胞」之名,而成為「原住民族正名運動」的重要推手。但當這位原住民的重要人物見到蔡政良時,卻不如平時那樣精神抖擻,只是帶著感傷地描述自己曾夢見未曾謀面的舅舅:「大雨中,舅舅深陷在泥巴裡,一直呼救,腳腫起來了不能走路,其他隊友本來要幫他,但沒有能力,所以就放棄他。」這個情節反覆出現在高正治的夢境裡。
加入的Gui Giling在戰爭時期被徵召到新幾內亞,就再也沒有回來。高正治表示,只要看到舅舅遺照,就會想到他的死,而這也成為他必須面對的內心重擔。
對此,蔡政良解釋,依據傳統,介達部落的首領原應該由Gui Giling擔任,但因為他在新幾內亞戰死,才由高正治的母親接下這個責任,後來再傳給高正治,「他(高正治)經常跟我分享舅舅的故事,還講到有哪些人也是高砂義勇軍。講著講著,他就問我,是否要再去新幾內亞,把他們的靈魂帶回來。」 蔡政良第一次到新幾內亞時,在威瓦克南方的男孩鎮(Boy’s town)舊日本海軍基地遺址,看到日本人在1969年所建的「英靈碑」。碑上展示了日軍遺留下的槍械兵器與鋼盔裝備。英靈碑的主體則刻有陣亡日軍的名字和部隊編號,周邊的小紀念碑則是草寫的追悼文。
「在這個日本人蓋的英靈碑上,完全沒有高砂義勇隊的名字,好像這些陣亡的日本軍人才是英靈,那麼,台灣的高砂義勇隊呢?難道是冤魂?一群被遺忘的冤魂。」蔡政良曾在2011年出版的《從都蘭到新幾內亞》一書中提到,日本戰敗,台灣也改朝換代,就在他們出發前往新幾內亞的前兩個月,國防部千里迢迢地跑到巴布亞紐幾內亞的拉包爾島,將當年在中國戰場被俘虜的中國軍人遺骨和魂魄,不辭千里迎到這批陣亡將士從來沒有來過的台灣,安奉在忠烈祠中,「那麼,當年在這裡戰死的數千名台灣原住民阿公們的靈魂呢?」
蔡政良在書中進一步表示,日本文獻紀錄中提到,當時戰場上有許多日本人的性命,是靠高砂義勇隊員的山林知識與「忠誠」而存活下來的,但是,「日本人在新幾內亞建立的紀念碑中,將高砂義勇隊遺忘了;現在的台灣政府,也遺忘了那些陣亡在新幾內亞的台灣原住民阿公的靈魂。」
豎立在新幾內亞的紀念碑,不只日本的英靈碑,澳洲也建了紀念碑,甚至被日軍帶去當奴工的印度人,也有屬於他們的紀念碑。而台灣兵,特別是高砂義勇隊員,則被各方遺忘了,什麼都沒有。
「我的成長過程中,幾乎沒聽過高砂義勇軍的故事。我只知道李光輝,但也一直把他當成英雄看待。」蔡政良坦言,1971年出生的自己,過去對這段大戰歷史確實無知,僅從新聞人物中獲得片段資訊。
1974年,藏身在印尼叢林30年的台籍日本兵李光輝(族名:Suniuo;日本名:中村輝夫)被印尼軍方發現,經媒體曝光後,才知他是被召入高砂義勇隊、隨日軍前往印尼打仗的台東阿美族原住民。李光輝在戰爭期間於印尼摩羅泰島(Morotai Island)失蹤,並被日本政府宣告死亡。這位「死而復生」的殘留老兵,於1975年1月回到台灣,並成為這段歷史的代表人物。 儘管透過閱讀和洛恩阿公的講述,蔡政良對高砂義勇隊的認識已有輪廓。但直到在都蘭部落遇到李光輝當年部隊的伍長,才發現真正當過高砂族陸軍特別志願兵的生還者,對李光輝明明是逃兵卻被視為英雄的社會觀點頗為不滿,甚至直指他就是個懦夫,「我那時才發現,圍繞高砂義勇隊這段歷史,仍有許多歷史觀的問題未被好好討論。」
在高正治的引薦下,蔡政良認識了卑南族利嘉部落的高砂義勇隊老兵陳德儀(族名:Kelasay;日本名:岡田耕治),並得知陳德儀曾用日語寫下戰場日記,便透過台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將這本日記翻譯出版。而兒時曾親眼見過高砂義勇隊集結出發的林哲次,自然成為譯者的不二人選,「因為他使用的日語,與日記中的日語屬於同一年代。」
蔡政良強調,無論是在二戰還是國共內戰期間,當時的國家機器與主流社會普遍將原住民族視為落後、野蠻,不僅認定他們需要被教化,甚至不將其當作是「人」,但為了打仗,這些平時被歧視與排斥的族群卻又被推上戰場:
「他們被殖民者強加了不屬於他們的『國家』概念,也被國族主義利用。然而,戰爭結束後,不論是日本還是國民政府都沒有對這段歷史進行反省、或至少給予公平的歷史評價,甚至還遺忘了他們。」 今日的國軍特種部隊中,有多達6、7成戰士是台灣原住民,而當年的高砂義勇隊卻連軍人都不是。蔡政良強調,「我們必須意識到,對大部分原住民來說,部落跟家園是很重要的,文化裡也有這樣的機制,讓他們願意為部落、為家園而戰,成為守護部落的勇士。」他更進一步指出,在台灣仍可能面對戰爭的當代,讓人願意上戰場的理由,不該只是空泛的國族主義。我們更該捫心自問:這是否是一個能夠彼此尊重、相互理解不同族群與文化的社會?我們是否真心把彼此當作家人,並共同把台灣視為自己的家園?
「就像當年許多不服氣、想要證明自己的高砂義勇隊員,那種為家園、為部落、為尊嚴而戰的勇氣與智慧。」
洪越评《清中叶作为写作主体的女性》︱是自我审查,也是自我赋能的“闺仪诗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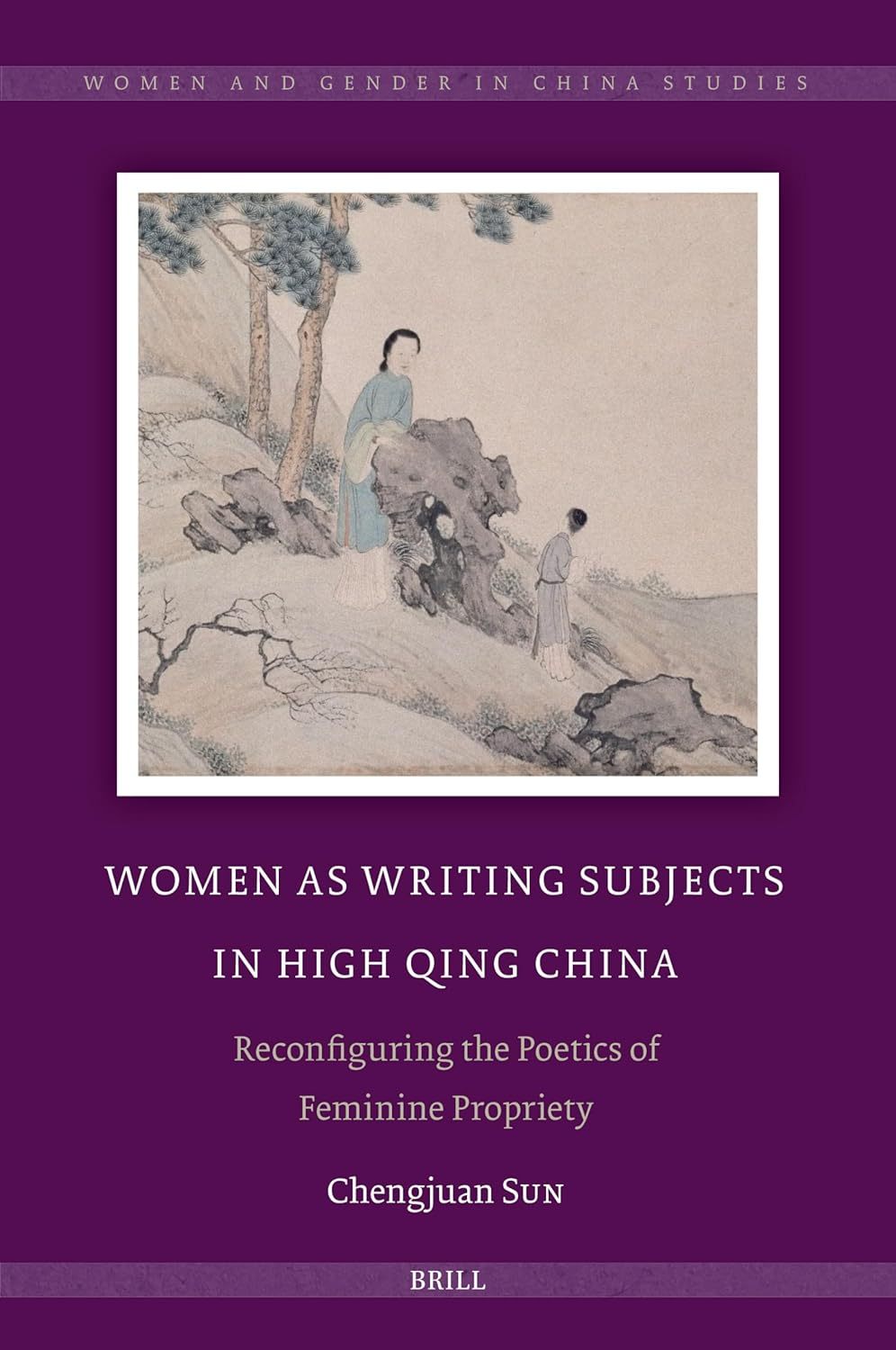
但实际上,近二十年来的北美明清女性文学研究告诉我们,女性诗词远比我们以前知道的丰富多样、有创造力。李惠仪(Wai-yeeLi)、钱南秀的研究表明,明清女性诗词的题材并不狭窄,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只写闺中生活;尤其是在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的易代之际,女作家更多写政治、写国难、写英雄气概,表达自己的政见、史识和豪情壮志。方秀洁(Grace Fong)、李小荣、杨海红的研究则说明,以闺阁日常为题材的女作家,在写作手法上也有诸多突破和发明,用以表达不同于男性文人的女性经验。到今天,这些作品是否值得作为文学来研究应该已经不是问题,我们需要做的是去阅读具体的作品,在大量的细读和比较的基础上分析明清女性诗词在艺术形式、表现手法、诗学思想方面的特点。这样的研究需要我们考虑这样一些问题:女作家如何因为性别身份的不同而对文学传统进行改造?具体来说,女作家如何在男性建立的文学传统中书写自我,在男性主导的文化里表达主体性?女性写作发展出哪些独特的主题和文学表现手法?女作家怎样改写文学传统来表达她们自己关心的议题?
孙承娟2024年在博睿出版社(Brill)出版的英文专著,Women as Writing Subjects in High Qing China: Reconfiguring the Poetics of Feminine Propriety,这里译为《清中叶作为写作主体的女性:重构闺仪诗学》,就探讨了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本书最有启发的地方是把明清女性文学当作文学来认真研究,以性别视角为基础,从具体作品出发分析女性文学与文学传统、女性经验之间的复杂关系,讨论女作家如何在男作家确立的诗歌传统中探索她们自己的诗歌语言。
孙承娟认为并非如此。她提出,清政府倡导的女性美德与闺秀写作之间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对妇德的要求使闺秀诗人在写作中进行“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不去写不符合社会礼仪和性别规范的作品。这无疑限制了题材的选择,比如她们一般避免直接写情欲,或者缠足、怀孕、生产这样的身体经验,不写钱,也较少表现愤怒、嫉妒和对抗的情绪。但另一方面,闺秀诗人也利用道德话语“自我赋能”(self-empowerment),表现为在妇德旗帜的庇护下追求自己的目标。比如,这一时期的女性诗集经常强调编纂目的是奉扬贞德,但集中收录的不少作品与贞德无关,这说明对妇德的肯定成为女性自我实现的修辞策略,或者说是一种道德包装,被用来提升女性文学的价值。在创作中,有些女作家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她们在诗中写自己是贤惠的妻子、贞洁的寡妇,是只写女性该写的文类和题材的作家,但同时也写那些不在妇德范围内、甚至与妇德相冲突的经验,比如向丈夫提出不符合他的利益的要求,追求名望和声誉,探索自我的精神世界,在文学和学术领域取得成就,等等。
这样的女性经验表达在明清以前的诗歌传统中是比较少的。诗歌传统中写女性的作品,比如宫体诗、香奁体和词,主要由男性文人创作,表现的是男性的关怀和兴趣,其中写到的女子往往是男性的欲望对象,对她们的描写经常是感官化、情色化的,尤其关注她们的容貌才艺,以及相思、激情和闺怨等男女之情。但闺秀诗人的身份是女儿、妻子、寡妇和母亲,欲望话语和她们的身份、她们想要表现的经验不完全符合,所以她们需要对诗歌传统进行改写,探索表达处于自己阶层和位置上的女性经验的诗歌语言。对这样的诗学探索,孙承娟发明了poetics of feminine propriety这个词来概括。
Propriety指通常被认为是正确的社会礼仪、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书中用poetics of feminine propriety指闺秀诗人的作品具有符合性别规范、认同社会规定的女性角色和女性美德的诗学特征。这里译为“闺仪诗学”。这本书的主体部分是对三位清中叶女诗人作品的分析和解读,这些个案研究展现了闺秀诗人如何在“自我审查”和“自我赋能”之间寻找平衡,如何改写诗歌传统进行自我表达。
书中讨论的第二位女诗人是骆绮兰,著有《听秋轩诗集》。她三十三岁守寡后参与诗词书画雅集,当时很多名士为她的画题诗,或者为她的诗作画、唱和、写序跋和题赞。孙承娟用三章篇幅分析骆绮兰如何在诗中戏仿和改造描写女性的诗歌传统,把自己的寡居生活表现为智力和精神上的自主自足。从骆绮兰对诗歌传统的改写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作为男性文人欲望对象的女性和作为写作主体的女性有多么不同。书中分析的一个有趣例子是骆绮兰对香奁体诗歌的改写。骆绮兰不写香奁诗中反复出现的被情色化的女性形象,而是把视线转向男性的欲望凝视所看不到的闺房物品,比如做女红用的针线。即便是写钗钏、耳环、鞋子这些香奁诗常写的物件,她也尽量淡化其情色意味,而是强调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功能。比如同样是写女子的鞋,香奁体鼻祖韩偓笔下的鞋是情色的,用来把玩的,“方寸肤圆光致致,白罗绣屟红托里”;而骆绮兰笔下的鞋是用来走路的,“行到花荫深径里,苍苔滑处自支持”,鞋子在湿滑的地上帮助女子保持平衡、站得稳,也象征着女子的独立自主。
书中分析的另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骆绮兰对李商隐《燕台诗》的模仿和改造。虽然骆绮兰在诗歌语言、结构和风格等方面模仿了《燕台诗》,但不同于李商隐写少女的迷乱激情,骆绮兰写幸福的妻子和忠贞的寡妇。对独守闺房这个主题,两位诗人也有截然不同的视点。李商隐写恋人缺席时女性的绝望,如“芳根中断香心死”、“一寸相思一寸灰”,这是闺怨诗传统对独处女子的惯常表现。骆绮兰也写女性剩了一个人,但表现她的坚韧,她应对孤独时的镇定自若:“一寸芳心铸成铁”、“女贞青玉凌霜雪”。孙承娟还指出骆绮兰用孤鹤比喻自己的寓意。因为早寡、没有子女(后来她领养了一个女儿),她好像离群的孤鹤一样悲伤;但同时,寡居生活提供的闲暇使她可以读书写作,可以享受“棋局茶烟”的愉悦,又好像孤鹤一般“逍遥”。孤鹤的意象突破了闺怨诗传统中女子因失去伴侣而孤独绝望的刻板形象。骆绮兰告诉我们,寡妇也可以有精神自由,有自我实现,可以有轻盈的人生:“此身自喜轻如鹤,佳处飞过偶一鸣”。
写作中自我审查与自我赋能并存的情况,在清代闺秀作家中应该说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在读古代女作家作品的时候,我们经常去寻找质疑或逾越父权社会中性别角色的直白表达。但孙承娟认为,闺秀诗人志不在此,这样的研究难以展开。很多时候,闺秀作家既认同已有的性别角色和女性美德,用社会规范要求自己,也借用道德话语表达自己的需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她们实现主体性的曲折方式。作者提出,那种认为履行传统性别角色就是保守、质疑就是进步的看法是有问题的,即便是对性别不平等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吴藻,也有履行孝女这个传统性别角色的一面。对社会规范和性别角色,闺秀诗人不是简单地服从或反抗,而是通过与规范博弈来发出自己的诗歌声音。博弈不只是挑战规范,也包括通过弘扬规范来追求自我实现。因此,闺秀诗人的作品经常既贞顺守礼,也以各种方式夹带私货,发出规范以外的声音。书中强调,“闺仪诗学”的生命力正来自这种既重申、又重构女性规范的张力;因此研究闺秀诗人的作品,重点不是去追问女性写作究竟是顺从还是抵抗父权秩序,而是考察女作家如何借用文学资源和思想资源、如何通过改写文学传统来进行自我表达和自我赋能。我同意这个观点,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书中讨论的三位女作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席佩兰和骆绮兰学诗画于文坛和书画界大家袁枚、王文治,拓展了她们社会交游网络;汪端出生于书香仕宦世家,对她影响很深的姨母梁德绳是当时著名的闺秀作家,公公陈文述是著名诗人。她们的位置和处境可能使她们有更多自我表达的空间。
从孙承娟的“闺仪诗学”论述想到,或许“女性诗学”可以作为考察明清女性诗词的一种角度。这里的“女性诗学”可以界定为由于男性建立的文学范式和惯例不能满足女性自我表达的需要,女诗人对文学传统进行突破和改造,探索自己的诗歌语言。“女性诗学”是复数的,处于不同时代、地域和处境中的女作家可能形成不同的诗学语言。例如,清中叶作为女儿、妻子、寡妇和母亲的闺秀作家有符合社会礼仪、性别规范的“闺仪诗学”,但同一时期的妾就不那么关注礼仪规范,侧室在家庭中较低的身份使她们可以更自由地写情欲、写身体。再比如,明末清初、清末民初经历战乱国难的女性,比和平时期的女作家更多写家国大事和英雄气概,因为政治的动荡促发女性在诗文中突破传统的性别角色。又比如,清朝北京的满族女作家和江南的闺秀作家又因为阶级、地域和民族的差异而选择不同的诗歌题材和写作手法。“女性诗学”的角度可以帮助我们探讨女作家因性别身份和经验的不同而对文学传统进行创造性改写的现象和成就,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思考明清女性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
深藏地下八百年,金代壁画重见天日

Art and Resilience Aligned at This Year’s BlackStar Film Festival 今年黑星电影节:艺术与韧性并存
在与艺术相关的电影中,有几部电影脱颖而出,证明了创作艺术所面临的挑战,无论是经济上的、情感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导演中村正探索了他在纪录片《第三幕》(2025)中所有这三种挑战,这是对他已故父亲罗伯特·A·中村的肖像,他是一位摄影师、电影制作人,也是一位教育家,有时被称为“亚裔美国媒体之父”。中村曾在马扎纳尔被监禁,马扎纳尔是二战期间美国建立的10个拘留营之一,他与人共同创立了视觉传播,这是第一个亚裔美国媒体艺术组织,并联合执导了1980年的亚裔美国故事片《旗帜飘扬》(1980)。中村坦率地谈到了他在马扎纳尔的拘留如何改变了他,在他心中灌输了自厌情绪和渴望成为白人的愿望,以及艺术和政治组织如何帮助他处理和转化这些痛苦的经历。
金钱是电影节上放映的两部与艺术相关的短片中焦虑的来源:LaTajh Simmons-Weaver的《预算天堂》(2025年)和DeeDee Casimir的《G’Baby的最后欢呼》(2025年)。这两个叙事都围绕着两位努力创作的年轻黑人画家展开。在《预算天堂》中,主角切斯特偷取艺术用品,并利用他们能找到的任何时间创作,为了绘画,他入住汽车旅馆房间两个小时。在切斯特入住汽车旅馆的场景中,可以看到对艺术世界的进一步致敬,柜台后面播放的视频让人联想到肯尼斯·安格的电影。海地裔美国导演DeeDee Casimir也在她的短片中展现了挣扎中的艺术家的真实写照,影片讲述了艺术系学生娜佳(由凯拉·阿米充满感情地饰演)的故事,她在花光了从祖母那里继承的现金后面临被驱逐的命运。
艺术家凯文·杰罗姆·埃弗森的创作涵盖绘画、雕塑和摄影,他在艺术中呈现了隐形的可见性。埃弗森执导了近 200 部实验电影,每部电影都源于他渴望捕捉那些令他着迷的劳动姿态和行为。他的电影不拘泥于流派区分,模糊了档案与当下、纪录片与虚构之间的界限。他创作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电影作品,这些作品沉浸在黑人生活的日常纹理中。《Dooni》是这一收藏中的一个受欢迎的补充,其中埃弗森将滑冰运动员的档案镜头与牧师沃尔特·霍金斯撰写的悼词并置在一起。



















